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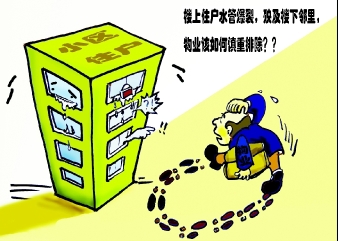
一、通行学说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法规定成立避险过当的条件是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但并未明确其内涵。学界在理解其含义时,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观点。
一是“小于说”。该说认为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是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⑴主要理由是:在客观后果上,紧急避险虽然损害了一定的合法利益,但保护了更大的合法利益,客观上对社会有益;在主观上,紧急避险造成较小的合法利益损害乃迫不得已,目的是为了保护更大的合法利益,动机和目的良好。因此,紧急避险在主客观上对社会有益,为我国法律所认可和提倡。⑵另外,我国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险是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为指导思想,要求一个人在面临危险时,牺牲局部的、较小的利益以保护整体的、较大的利益,使合法权益免受损害或减少损害。我国刑法决不允许以牺牲他人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不允许为保全局部、较小的利益去牺牲整体、较大的利益。⑶
二是“不超过且必要说”。该说认为“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是指在所造成的损害不超过所避免的损害的前提下,足以排除危险所必要的限度”。⑷其与“小于说”之不同有二:其一,紧急避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损害同等法益的,也不一定超过了必要限度”。⑸主要理论依据为零损害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根据零损害理论,在需要保护的两种利益完全等同且必然牺牲其中一种利益时,牺牲何种利益无实质区别,不能要求避险人对任何一种利益优先保护。因为从法益比较衡量的角度来看,保护法益和牺牲法益等价,就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冲突结果为零。既然为零,就意味着没有出现必须作为刑法处罚对象的法益受到严重侵害的负面结果。⑹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在保护的法益与牺牲的法益价值相同的情况下,应当考察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⑺其二,即使所造成的损害不超过所避免的损害,但损害不必要,超出足以排除危险的限度,成立避险过当。“当紧急避险只需要损失微小的合法权益就可以避免危险时,如果损失了较大的合法权益,尽管损失的合法权益仍然小于保护的合法权益,避险行为也超过了必要限度,构成避险过当。”⑻因为紧急避险是两种合法利益之间的冲突,应当用尽可能小的损害去保全较大的合法利益,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的,不一定都属于必要限度之内。⑼
上述两种观点中,“小于说”作为“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践对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的认识极为一致”⑽的学说,乃通说。笔者认为,“小于说”并没有揭示“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真实含义,自身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
首先,“小于说”的立论依据不充分,且与民法、刑法等相关规定不协调。
“小于说”认为,紧急避险的本质是为了保全较大的权益而牺牲较小的权益,故其限度取决于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与所避免的损害之比较,这种理解并不确切。刑法规定紧急避险制度,本质上是为了防止合法利益免受危险损害,避免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这与“保全较大的权益而牺牲较小的权益”并不具有等同关系。另外,“小于说”认为我国刑法认可并提倡紧急避险,是因为其在主客观上保护了更大的合法利益,对社会有益。这种理由也比较勉强。根据《刑法》第21条的规定,紧急避险与避险过当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解决的是罪与非罪的问题。“小于说”虽然认识到刑法鼓励、支持、保护整体上有益于社会的紧急避险行为,却没有说清楚整体上对社会没有益也没有害或者有害于社会的避险行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而这些行为之性质在判断紧急避险的限度时是必须要解决的。
“小于说”还认为,我国刑法不允许为保全局部的、较小的利益去牺牲整体的、较大的利益,这也值得商榷。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该规定表明,民法上的避险过当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民法上的避险过当当然包含为保全局部的、较小的利益去牺牲整体的、较大的利益的行为,但在性质上与刑法上的避险过当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民事违法行为,后者是犯罪。在刑法上,行为只要不构成犯罪,都是允许的。为保全局部的、较小的利益去牺牲整体的、较大的利益只要不构成犯罪,即使是民事违法行为也是刑法所允许的。不难发现,“小于说”无法解释民法中的紧急避险为什么不承担刑事责任。
事实上,我们在阐释法律时,恰恰应当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去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作的取舍。⑾“小于说”对紧急避险限度的理解是在机械规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没有顾及刑法的相关规定,必然造成规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小于说”所蕴含的逻辑是,避险过当因为从整体上说并非是有益于社会统治秩序,所以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当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时,成立紧急避险;否则,成立避险过当,承担刑事责任。然而,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某一行为即使对社会造成危害,只要情节显著轻微且危害不大,就不能以犯罪论。这意味着即使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等于或大于所避免的损害,只要情节显著轻微且危害不大,是不能以犯罪论处的。
其次,“小于说”在本质上属于客观判断,无法解决某些具体问题。
“小于说”所指的损害,注重的是法益的性质,是一种确定损害大小轻重的客观标准。⑿在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评价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与所避免的损害之大小,主要依据法益权衡原则。“法益衡量依据客观的标准,即所考虑的两个法益同是属于一个人而行为人又是通常人时,哪一个法益更重要按照经验法则来决定,行为人的特殊兴趣、倾向等都不是决定问题的标准。”⒀应当说,法益权衡原则根据客观损害结果进行比较,可操作性强,判断起来相对容易。但是,该原则也招致许多质疑。“法益权衡说是从‘所有的法益都可以计量价值’的前提出发的,为了大利益而牺牲小利益时,还把保留相差的利益看作是文化秩序的要求,这完全是商人的观点,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倾向,所以这种立场是私法部门发展起来的原因。”⒁刑法保护的法益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仅仅根据客观标准有时很难权衡。例如,因为自己的小孩突发疾病,不马上送往医院便有性命之忧,因而无证驾驶、超速驾驶,或者酒后驾驶,将小孩送到了医院。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为了救助自己小孩的生命而违反《道路交通法》等相关交通法规。这里侵害的法益属于社会公共安全这种抽象的法益。对此,往往难以比较二者之间的优劣。⒂总的来看,立足于客观判断的“小于说”存在形式化、量化等缺陷,只能解决部分避险行为的限度问题,有所不足。
“不超过且必要说”作为近年来的有力学说,弥补了“小于说”的某些不足,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其缺陷主要在于以下方面。首先,与“小于说”一样,“不超过且必要说”的立论依据因脱离刑法规定而难免让人质疑。其次,“不超过且必要说”在理论上也缺乏说服力。零损害理论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各种影响价值评价的因素,不能体现对避险行为性质的全部评价。“受到保护的利益和受到侵害的利益相等时,韩国以往的通说是认定相当性的。但是均衡性原理意味着优越利益的原则,在相同利益之间是不承认这种关系的,因此在这种情况,应当视为不阻却违法性。在均衡性的判断中,以往的法益均衡理论应被包含性的利益均衡的原则所替代,故不仅是关系法益,危险的程度和保护的价值也要综合来判断。”⒃至于期待可能,本指从人格体的角度分析具有不可期待性,体现出一种客观、普遍的人格特征。“在此不谈及那些零散的、私人的、秘传的、虚假的和类似的定义,则这种期待作为一般的看法表现出来,并且在下述意义上是一种客观的数值:它不依赖于被作为人格体来定义的人的承认,也就是说,即使这个人不把自己理解为主体,也会发生这种期待。”⒄在损害同等法益时,是否具有不可期待性,在不同的情况下是截然不同的,并不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如果受到危险威胁的是本人或与本人有特殊关系的人(如儿子、亲朋好友),行为人往往不可能有正常的动机形成过程;但如果涉及一个不熟悉的外人,就很难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解释。”⒅再次,“不超过且必要说”因在过当理论中与“小于说”竞合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共同的缺陷。最后,该说还认为只要造成了不适当损害,不管其程度如何,都可成立避险过当,这与《刑法》第13条的规定也存在冲突。
二、判断紧急避险限度的根据
从刑法规定来看,“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应当分两部分进行理解。
1.“超过必要限度”。在理解上首先应该弄清楚是什么行为超过必要限度。毫无疑问,当然应当是指避险行为。紧急避险的目的是通过避免危险发生而保护合法利益,评价其超过必要限度的立足点只能是在为了避免危险发生而对第三者的合法利益所造成的损害上。由于“超过必要限度”后而有“不应有的损害”之规定,故“超过必要限度”只能是指为了避免危险的发生而实施的行为限度。例如,制止动物侵袭的危险,只需将动物打伤即可阻却,但却将其打死,故造成动物死亡的行为便属于超过必要限度。因此,“超过必要限度”是相对于避险行为而言的,是对避险行为的要求。
2.“不应有的损害”。与“超过必要限度”相对应,这里的“不应有的损害”是针对行为后果而言的,即对其他合法利益造成不必要、不恰当的损害。“不应有的损害”与“超过必要限度”既密切相关又有所不同: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避险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就不存在“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只有避险行为“超过必要限度”,才会产生“不应有的损害”。但是,“不应有的损害”毕竟是一种行为后果,与避险行为存在性质上的不同。不应有的损害后果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满载20000吨货物的货船在海上航行时突遇狂风暴雨,有倾覆危险,只要将其中的5000吨货物卸下便足以防止危险发生,卸载的超过部分当属于“不应有的损害”,这种损害既可以是1吨货物,也可以是15000吨货物,相去甚远。由于避险过当成立犯罪,而犯罪成立是由行为事实和刑法规范共同决定的,因此,这里的“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应当立足于事实与法律加以综合判断。立足于客观事实,“不应有的损害:”应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将合法利益的损害与危险将要造成的损害相比超过一定程度,这是“小于说”所主张的,义如,某载满货物的大型货船在海上航行时突遇狂风暴雨,如果不舍弃货物将会发生船毁人广:的后果,此时,为了保证船只和人员安全,即使舍弃全部货物,也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二是造成合法利益不应有的损害,即对所主张合法利益的损害本可以更小却造成较大危害,那么较大的危害显然属于“不应有”,这为“不超过且必要说”所关注。例如,在上述案例中,如果舍弃部分货物就足以避免灾害发生,那么舍弃全部货物显然属于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这两种“不应有的损害”的区别在于,前者立足于两种损害的对比,并不考虑所造成的损害是否合适;后者侧重于“造成的合法利益的损害”本身,并不涉及两种损害的对比。立足于刑法规范,“不应有的损害”是决定避险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损害。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是社会危害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因此,即便所造成的损害大于危险将要造成的损害或者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只要社会危害没有达到一定程度,避险行为也不构成犯罪,这是“不应有的损害”的法律含义。又如,在上述案例中,假如只要抛弃价值5万元的货物就能避免船毁人亡,而行为人抛弃了价值5.1万元的货物,由于超出必须抛弃的货物部分价值不大(只有1千元),因而可以不认定为避险过当。
由上可知,成立紧急避险首先必须遵循适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又可称为最轻微侵害手段或尽可能微小限制的原则,意指为保护某种较为优越的法价值须侵及一种法益时,不得逾越达此目的所必要的程度。⒆根据该原则,在紧急避险的场合,如果能将损害控制在最小限度,那么基于功利主义的立场,行为人即使不能将利益最大化,至少应当将损失最小化。否则,就可能成为国家发动刑罚权的理由。“生活中充满了两难选择,不论做什么,总会产生某种不希望的结果。如果我们不能将利益最大化,那么功利主义的原则告诉我们必须将损失最小化。”⒇适当性原则作为紧急避险合法化的根据,是判断紧急避险是否超过限度的首要标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适当性原则通常是决定紧急避险合法化的依据,这不但在理论上形成了共识,在规范中也得到了体现。“总的来说,德国法演进的基础,以承认危害最小化的集合性利益是法律的一种更高的超规范原则。”(21)紧急避险作为刑法赋予公民的一项特殊权利,涉及到损害第三者的合法权益,当避险人能够将损失最小化但却肆意扩大时,他显然是在滥用权利,这无异于犯罪。可见,遵循适当性原则,将损失最小化,是防止滥用权利的当然要求。“为了改变神圣的极端立场,德国的刑事律师已经引入了民法的‘滥用权利’理论。如果承认财产所有人在原则上有权杀死逃跑的小偷,那么,当这位所有人以一种滥用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他也是在实施犯罪。”(22)之所以要防止滥用权利,是因为人们注意到紧急避险作为一项合法权利,用之不当会造成权利滥用之弊端。“在巴伐利亚州的判决中,法院虽然认定使用武力保障一个停车位是在行使紧急防卫权,但它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这一防卫权利被滥用了,因为防卫人‘施加的危害与侵害的威胁不成比例’。这个判例经常被引用,以支持一个渐趋一致的意见:滥用权利原理,限制了紧急防卫权的行使。”(23)德国《刑法》第34条将“要考虑到所要造成的危害的法益及危害程度”(24)作为紧急避险阻却违法性的条件,则可视为适当性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在法国,学界通常认为“紧急避险所使用的手段与面临的危险的严重程度应当相适应”。(25)《法国刑法》第122—7条明确了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同时在“但书”中规定“所使用的手段与受到的威胁的严重程度不相适应之情形除外”。(26)在意大利,通常认为紧急避险“‘必要的行为’包括三个构成要素:‘被迫’、‘必要’和‘适当”’。(27)《意大利刑法》第54条规定,紧急避险“只要其行为与所面临的危险相对称,不受处罚”。(28)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在传统上更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均衡与刑罚适用的合理性,故一直强调避险损害必须适当,防止权利被滥用。众所周知,英美法系国家犯罪成立要件包括本体要件和合法的抗辩事由。“在理论结构上,犯罪本体要件(行为和心态)为第一层次,责任充足条件为第二层次,这就是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双层模式。”(29)其中,合法的抗辩事由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证明适当。“以‘证明适当’申辩的被告人声称,在他所处的那种特定情形之下,其行为尽管可能满足了犯罪构成的每一要素所要求的条件,但在法律上并没有过错……被告人在‘证明适当’的条件下的行为可能是值得他人仿效和赢得全社会的鼓励的,但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它是可允许的,并为社会所接受的。”(30)在英美法系国家学者看来,根据适当性原则,紧急避险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它对保护或者促进受到威胁的利益必须是必要的;二是它所引起的损害与即将发生的损害或者促进的利益必须是相适应的或者是合理的。(31)而避险所引起的损害与危害将要造成的损害相适应或者合理的表现,便是在能够避免危险造成的损害发生的情形下,避险造成的损害应当最小化。“当行为人受到威胁必须立即作为时,他有权使用的仅仅是自我保护所必需程度的暴力。即使多数人认为使用更大的暴力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个别行为人使用较小的暴力就可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话,他使用了较大的暴力就是不正当的。”(32)“紧急避险是在危害的最小化中谈论集合性利益的话语的。无视这个视角上的不同,将使这个已经影响并决定了刑法历史的思想变得无足轻重。”(33)
也有人对适当性原则持反对意见。“一个人可以通过对各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造成较小的损失而防止更大的损害。换言之,在该情势下有几种实行紧急避险的方式。这种情况下紧急避险的选择权属于行为人。如果存在几种实行紧急避险的方式,行为人所选择的行为方式造成的损害不是最小的,那么他的行为也是合法的。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所造成的损害(损失)小于所防止的损害……假如规定在紧急避险时必须采取最佳方式造成最小的损害,就会导致这种制度名存实亡。”(3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紧急避险虽然是刑法规定的一项权利,同时也是一项义务。根据刑法规定,行使紧急避险权的前提条件是保护合法权益免受危险侵害。由于紧急避险所损害的第三者利益也是一种合法权益,因而同样需要避险人全力保护。如果避险人可以将对第三者权益的损害降到最低,却造成更大的损害,是与避险目的相矛盾的。因此,行为人实施避险行为时,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不能自由选择。其次,如果因为法律赋予了紧急避险的权利,就认为具有侵害第三者合法权利的选择权的话,必将导致第三者权利处于“危险”中,造成损害的恶性循环。“如果人们被强制采取某种行动而不管其后果如何,胁迫和紧急避险最多是对非法的行为的辩解。”(35)因此,要求避险人恪守一定的损害界限完全必要。最后,适当性原则只是要求避险人在紧急避险时,在其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减少所造成的损害,并非超出其能力要求采取最佳方式,因而不会导致这种制度名存实亡。
三、紧急避险适当性的评价标准
(一)紧急避险适当性的评价属于价值评价
在判断紧急避险限度时,“小于说”与“不超过且必要说”均选择将造成的损害与避免的损害进行比较作为主要依据。虽然后者意识到不适当损害在其中的作用,但也只是限于所造成的损害小于避免的损害这一特定情形之下。因此,两种学说在本质上还是权衡法益,通过对损害进行客观比较和判断,确定紧急避险的限度。在“小于说”与“不超过且必要说”看来,两种损害相衡主要是客观损害相衡,至于其所体现的价值内容的重要作用,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造成学界在理解紧急避险的限度时,往往陷入机械的逻辑规则束缚之中,背离了刑事立法的本意,难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笔者认为,紧急避险的限度所涉及的两种损害相衡,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权衡,不能单纯通过损害大小之比较或者以此为基础,将之解读为形式化、量化的客观判断。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紧急避险两种损害的比较为价值权衡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司法实践中,面对造成损害与避免损害的法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有时很难对各自的利弊得失进行客观比较,这种情况在不同法益之间比较常见。例如,在健康权和财产权之间,就很难通过形式的客观依据判断利益的大小。就是在同种性质的法益之间,有时也很难进行大小轻重的比较,如在身份权和名誉权之间的比较就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往往会以损害双方的社会价值为基础,进行整体评价并作出判断。例如,如果危险可能造成被害人重伤,行为人为了避免被害人重伤结果的发生,损害他人价值10万元的财产,并在一般人的社会价值观念上是必要且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应当成立紧急避险。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为了避免被害人重伤结果的发生,损害他人价值数千万元的特别巨额的财产,并在一般人的社会价值观念上是完全没有必要且不可理解的,则应当成立避险过当,承担刑事责任。不难看出,这种判断不是具体、客观、局部的利益大小比较,而是抽象、综合、整体的社会价值的比较,是一种价值判断。除此之外,对于无法进行客观判断的法益,只能通过社会价值比较才能判断紧急避险的限度。例如,文物就需要通过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艺术等价值的综合评估,测算出整体的社会价值,作为损害大小的判断依据。总之,紧急避险限度之判断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其次,紧急避险两种损害的比较为价值权衡是刑法理论发展的经验总结。
在国外刑法理论中,紧急避险限度判断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已得到普遍认可。“在解决法益价值衡量时,既然不可能有抽象性、一般性的基准,则应就各个具体事件,依法秩序整体之精神,做合理之判断,即判断时不应考量行为人之主观价值,而应当考量以社会一般通念为基础之客观、合理的价值。”(36)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典中,也有将造成的损害与避免的损害进行大小比较后确定紧急避险的限度的规定。如《日本刑法典》第37条对紧急避险限度的规定是,“所造成的损害不超过其所欲避免的损害。”(37)以往,日本学界在理解这一规定时往往依据的是法益权衡原则,但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法益权衡原则的局限,并在法益权衡之外,就紧急避险的限度提出各自见解。如野村稔认为,“对于法益的均衡性子以现实的评价时,不同的法益之间很难判断其优劣,因而只能根据基于宪法的法秩序原理的以自律的人格的发展为最高价值的具体的社会观念予以判断。”(38)大谷实指出,“为了成立紧急避险,仅具备形式的要件还不够,还必须对避险行为整体进行考察,要求在实质上也具有社会相当性。这一要件就是紧急避险的社会相当性。”(39)无论是基于宪法的法秩序原理下的具体社会观念,还是根据整体考察的社会相当性判断,本质上都是一种整体、综合的价值判断。在英美法系国家,人们也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要想通过形式化、量化的利益权衡对紧急避险限度加以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利益的无形化使得精确权衡很难实现。实际上,对于所有的正当性理由来说,虽然冲突的利益可以被分辨,但它们罕能被充分定量化以允许在适应性评定上作出完全精确的比较。”(40)利益权衡只能是法官或者陪审团作出的价值判断,“根据事实的合理表现,问题不在于被告人是否认为他作出了正确选择,而是‘被告人的价值判断在事实上是否正确’,这由法官或者陪审团来决定。在作出价值决定时,法官或者陪审团可以适用功利主义价值标准,或者让判断基于‘这种情形下在道德上什么是正确和合适的行为’。”(41)
(二)紧急避险适当性的评价标准
作为一种价值判断,认定紧急避险是否适当,需要考虑众多的因素,这大大增加了紧急避险限度判断的难度。“紧急避险问题上存在的最大困难仍然是,如何评判行为人所使用的手段与危险的严重程度之间是否相适应。”(42)一般来说,紧急避险的适当性评价标准包括一般标准和特殊标准。
1.适当性的一般评价标准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通常认为,“所谓‘只要不超过限度’,指侵害利益和保护利益相比,前者不超过后者的意思。利益的比较,应根据客观标准进行。因此,在同一利益上以量的大小为标准;在不同的利益上,保护各种利益的犯罪的法定刑的轻重,成为大致的标准。当然,法定刑不一定反映了利益的大小。另外,个人利益和各种公共利益的关系也不明确。因此,难以得出一般标准,应当按照具体事例,根据社会一般观念,判断利益的大小。”(43)英美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也认为,通过利益衡量判断紧急避险限度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美国刑法理论上认为,在进行利益衡量时,应遵循以下三项原则:第一,价值判断最后取决于法院的意见,而不是当事人的看法;第二,人的生命价值高于财产;第三,生命等价,即人的生命价值不因人的种族、年龄、健康、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异。”(44)可见,尽管人们不将造成的损害与避免的损害进行客观比较判断作为紧急避险限度认定的唯一标准,但通常认为这是判断紧急避险限度的基础之一。原因在于,尽管紧急避险限度的判断属于价值判断,但是行为的价值本身便是一个抽象和模糊的概念,有时需要有所依托才能更好地认定,将造成的损害与避免的损害进行客观比较判断,正是这种依托的支点。以此为依据,才能进一步分析两种利益之社会价值的大小,完成对其的价值评判。因此,紧急避险限度的价值判断,实质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客观判断,即将造成的损害与避免的损害进行客观比较,这往往是判断紧急避险限度的前提和基础;二是价值判断,即综合一切影响两种损害的社会价值的主客观因素,分别加以分析,并就紧急避险的整体社会价值作出最终判断。客观判断有时是认定紧急避险限度的必要条件,价值判断则是认定紧急避险限度的充分条件。“人们在这里不再仅仅要求一种财富的权衡,而是也要求一种广泛的利益权衡,在这种利益权衡中,除了别的之外,法益的对比仅仅应当表现为一种要点。”(45)
在大陆法系国家,根据法益权衡原则进行的客观判断,一般承认生命法益高于身体法益,身体法益高于财产法益,公法益高于私法益。(46)对此,我国学者予以了进一步诠释,“一般来说,同种类的权益大小往往容易比较,比如说财产权益以财物价值大小即可确定哪一种财产权益大,,相反,不同种类的权益大小则很难比较。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认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个人利益中,人身权利高于财产权利;在人身权利中,生命权高于健康权,健康权高于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权高于名誉权。”(47)当然,由于行为及其客观损害结果是影响法定刑轻重的主要因素,因而根据法定刑权衡法益价值大小也被认为是可取的。“利益的比较,应根据客观标准进行,,因此,在同一利益上,以量的大小为标准。在不同利益上,保护各种利益的犯罪的法定刑的轻重,成为大致的标准。”(48)
2.适当性的特殊评价标准
至于影响造成的损害与避免的损害的社会价值因素,则非常之多。除了需要考虑危险源、危险的紧迫程度、强度、避险行为人的情况、行为人的认识水平、行为能力、应急能力等紧急避险的一般因素外,还需要考虑道德伦理、文化价值观念等对行为的社会价值具有影响的特殊因素。一般因素附随于不同情形下的紧急避险而必然存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殊因素虽然不是附随于紧急避险而必然出现,却具有通识性,在判断紧急避险限度时需要特别考虑。这些特殊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善良风俗与美德。作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评价因素,社会善良风俗与美德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判断损害大小时应当考虑在内。“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即为支配法律之根本,故行为之违法性,应为实质的观察,而不应单为形式的观察。行为触犯刑法,仅可谓为形式意义之违法,必更于法律上不应容许,始可谓为实质意义之违法,此则不仅单依法令之形式决定之,更应依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观念决定之。”(49)一般来说,即便是同质的法益,如果损害某种法益是根据社会善良风俗与美德作出的,那么损害的整体社会价值会因此而相应减轻。“当对被害人利益的侵犯在其他情况下会是必要的时候,紧急状态下行为人的行为就会导致对被害人利益的一种比较轻微的侵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能通过第34条来使对特别规范规定的法定侵犯条件的忽视得以正当化。”(50)例如,当精神病母亲缺乏自保能力时,私自外出游荡就会有各种危险。此时,儿子将其禁闭于家中,剥夺其人身自由,就被认为是正当的。理由是尽管母亲游荡所受的损害并不确定,但为了母亲的安危剥夺其人身自由,是儿子竭尽孝心和善待的举动,完全值得理解。
二是第三者的自律权。在日常生活中,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需要对他人身体、财产决定、支配自由等权益予以起码的尊重。紧急避险时,行为人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转嫁自己面临的风险,就必须考虑被转嫁风险的人对自己利益的决定权,是为自律性原则。该原则主张,在将危险转嫁给第三者的紧急避险的场合,必须将第三者的人格自律性即个人生命、身体以及正在使用的雨伞、衣物、住宅等与个人的决定自由相关的利益考虑在内。任何人没有忍受来自他人的、对自己的人格的自律性所进行的无理侵害的义务,人人都有自己决定权,对他人生命、财产、身体等的侵害,同时也意味着对这种自律性的侵害。这种自律性与其他具体法益一样,是在进行利益衡量的时候,必须考虑的第三者的利益。(51)在违背自律性原则的情况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会更突出。因为对他人自律权的侵害,不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侵犯他人对自己的财产等的自行支配自由,还会成为侵害者恶意转嫁风险的理由,这显然不是刑法规定紧急避险制度的目的。“由于利益衡量包含自律性,第三者的利益的比重变得重起来。”(52)第三者利益比重的抬升,使得即使造成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亦不能成为排除犯罪性的理由。例如,为了避免自己价值10万元的名贵服饰遭受火烧,将第三人价值8万元的服饰作为“挡箭牌”,就不能成立紧急避险。需要注意的是,侵犯自律权阻却紧急避险的成立,也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即只是在权益相对均衡或者对称的场合适用,否则可以成立紧急避险。例如,由于无家可归而窃取他人食物或者侵入他人住宅者,因为侵犯他人的自律权而不能成立紧急避险。但是,如果无家可归者在面临死亡(饿死或者冻死)或者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形下,窃取他人食物或者侵入他人住宅就可以成立紧急避险。“现在的法律也许是,如果获得食物和进入房屋是防止因饥饿或寒冷而导致死亡或严重损伤所必需,则存在着环境胁迫的辩护理由;但如果仅仅是为了防止饥饿或因寒冷、无家可归而带来不舒适则不存在辩护理由。”(53)
三是社会共同体责任。任何社会都有责任对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提供保护,这便是社会共同体责任。当公民或社会成员遭受某种危难时,如果对这种危难的解救属于社会共同体责任,不应当由无辜的第三人来担负利益损害,这便是社会共同体原则。该原则表明,如果避免危险是社会共同体责任,就会改变法益之社会价值的对比。例如,为了挽救缺钱治病的濒死患者,从百万富翁那里拿走了以合法方式不可能得到的钱,用来支付为挽救生命所需要的手术费或者疗养费,这种行为就缺乏作为避免危险手段的适当性,因为消除重病患者无钱医疗这样的紧急情况属于社会共同体的任务。社会共同体未尽到责任的,不能由个别人(百万富翁)做出牺牲,要求其承担超出范围的容忍义务。(54)
四是法益的重大属性。生命权重于健康权,健康权重于财产权,这是一般原则,但也有例外。如果所避免的损害特别重大,或者具有特殊意义,即便是财产权益或者其他权益,也应当允许最低程度地对健康以及人格身份等权利造成损害,作为排除犯罪性的理由。(55)这种情形被李斯特称为“超越法律之紧急避险”。他认为,为挽救重要国家利益,尤其是为维护国家财产,防卫叛国或叛州的行为,如果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不可能实施正规的国家防卫行为,且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又是紧迫的,允许个人损害他人的法益。(56)特别重大的法益优先考虑,意味着即使对人身权益造成侵害,有时也可以被允许。“尽管在通常情况下,身体健康的价值高于单纯的物之价值,但是在一起火灾事故中,如果看热闹的人挡住了帮忙的邻居,那么,仍然允许把他撞到一边,从而‘伤害’(misshandeln)其身体(《刑法典》第223条)。”(57)我国学者通常也认为,“如为保护个人生命损害数以亿计的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或者是数以百计的人身受重伤,便很难认为还在避险的必要限度之内。”(58)重大的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优先权表明,不同性质的法益之间的轻重比较有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五是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社会群体利益,是维护国家、社会秩序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也是人们必须遵循的准则。即便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的瑕疵,也被认为应当得到尊崇,这是维护社会群体利益必须付出的代价。公共利益的这种独特属性,使得其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其社会价值往往被认为更为重大和突出。如果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即使个人利益受到政府机关合法侵害时,体现出某种不公正,也必须忍受,不能实施旨在牺牲公共利益的紧急避险。例如,司法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合法的拘留、逮捕,甚至执行刑罚,对个人自由权造成损害,虽然被害人不构成犯罪,已经生效的自由刑也必须执行,除非依法撤销有罪判决。如果被害人伤害监管人员越狱,不能成立紧急避险。出于同样的道理,家庭成员也必须接受根据法治国家的程序对某一家庭成员科处的法定刑。(59)
六是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基本人权是社会存在的个人或其群体享有的“人之所以为人”、“把人看作人”的最起码、最基本的人格、身份、生存、安全等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基本人权是根本性和普遍性的人权,是享有其他人权的基础,在一切人权中处于优先保障地位。《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就明确宣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在紧急避险的价值判断中,基本人权必须优先考虑,不得以紧急避险为由肆意加以侵犯。例如,人格尊严权利是自然人的基本人权,在进行紧急避险时,不应当以这种权利处于微弱地位而进行损害他人人格尊严的紧急避险。“然而,恰当性条款还是具有一种功能的。它超出了一种对谨慎地进行利益权衡的呼吁,从一开始就在法律咨询中发挥了作用:这种指示性作用指出,保持自然人的尊严是无法通过有限的权衡达到的。”(60)典型的例子是,甲属于RH阴性AB型血,因失血较多急需输血(只能输入同型血)。由于仅发现乙具有同一血型,未经乙同意强行从其身上抽血,就不能成立紧急避险。因为虽然仅有乙一人符合输血条件,且抽取部分血液对乙的生命不会造成多大妨碍,但未经乙同意强行从其身上抽血,事关乙的人格尊严,无法通过利益的简单权衡比较轻重,即便避免损害的是生命权也是如此。否则,被侵犯的人格尊严权可能导致连锁反应,致使基本人权受到严重挑衅,这是不允许的。又如,为了救出被黑社会性质组织绑架的人质,避免其生命受到伤害,而通过刑讯逼供迫使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说出人质的藏身之所,就不能成立紧急避险。因为刑讯逼供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身心健康与人格尊严,不应该以紧急避险为由加以危害。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⑵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
⑶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1页。
⑷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⑸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页。
⑹参见黎宏:《犯罪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页。
⑺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63页。
⑻王作富主编:《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⑼参见张明楷:《犯罪论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页。
⑽同前注⑶。
⑾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⑿参见王瑾:《中华刑法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233页。
⒀[日]泷川幸辰:《犯罪论序说》,王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⒁同上注,第102页。
⒂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⒃[韩]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韩相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⒄[德]京特·雅科布施:《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冯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⒅[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⒆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5页。
⒇[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梁根林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21)[美]乔治·P·弗莱彻:《刑法的基本概念》,蔡爱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22)同前注(21),乔治·P·弗莱彻书,第177页。
(23)[美]乔治·P·弗莱彻:《反思刑法》,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35页。
(24)《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25)[法]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则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
(26)《法国新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27)同前注⒅,杜里奥·帕多瓦尼书,第159页。
(28)《最新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29)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30)[美]道格拉斯·N·胡萨克:《刑法哲学》,谢望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31)参见[美]保罗·H·罗宾逊:《刑法的结构与功能》,何秉松、王桂萍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32)同上注,第112页。
(33)同前注(21),乔治·P·弗莱彻书,第186页。
(34)[俄]Н·Ф·库兹涅佐娃、И·М·佳日科娃主编:《俄罗斯刑法教程(总论)》(上卷·犯罪论),黄道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68—469页。
(35)同前注(30),道格拉斯·N·胡萨克书,第325页。
(36)陈子平:《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37)《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38)[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249页。
(39)[日]大谷实:《刑法总则讲义》,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40)同前注(31),保罗·H·罗宾逊书,第113页。
(41)[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精解》,王秀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42)[法]让·帕拉德尔、贝尔纳·布洛克:《〈新刑法典〉总则条文释义》,同前注(26),罗结珍译书,第307页。
(43)马克昌主编:《外国刑法学总论(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44)赵秉志主编:《英美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45)[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46)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47)刘明祥:《论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48)同前注(31),保罗·H·罗宾逊书,第276页。
(49)陈瑾昆:《刑法总则讲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50)同前注(46),张明楷书,第482页。
(51)参见[日]山中敬一:《刑法总论》,成文堂1999年版,第497页。转引自[日]川端博:《刑法总论》,余振华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4页。
(52)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53)[英]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陈兴良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54)参见[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55)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只是强调可以对健康以及人格身份权利造成损害,不能包括生命权。任何时候都不能允许以保护重大法益为由,通过剥夺他人生命加以紧急避险。关于该问题,下文将予以详细论述。
(56)参见[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57)[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58)同前注⑴,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书,第152页。
(59)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84页。
(60)同前注(46),张明楷书,第496页。
原标题:紧急避险限度的适当性标准
来源:《法学》2013年第3期
牛律师刑事辩护团队编辑
牛律师刑事辩护网www.lawyer123.cn,依据最权威的法律法规,秉持最科学的刑辩技巧,坚持术有专攻成就刑事辩护品牌成功案例。为正在身陷囹圄或因犯罪即将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亲友提供无罪、罪轻、减轻处罚的服务。牛律师刑事辩护精英团队,专注刑辩领域,案例成就金牌!
服务热线:4006066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