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有哪些?---牛律师刑事辩护团队律师告诉您
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1)必须针对正在发生的紧急危险。如果人的行为构成紧急危险,必须是违法行为;(2)所采取的行为应当是避免危险所必需的;(3)所保全的必须是法律所保护的权利;(4)不可超过必要的限度,就是说,所损害的利益应当小于所保全的利益。紧急避险不负法律责任。在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不得在发生与其特定责任有关的危险时实行紧急避险。防卫过当行为造成严重伤害后果而致防卫人构成犯罪的只应该定性为过失犯罪
对于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理论认识,无论认为防卫过当行为之罪过是过失、是故意还是既可过失又可故意或既有过失又有故意,似乎都忽略了一项重要的内容,即防卫过当之过当的实质是什么。在司法实践中很有必要对这些没有作出统一标准但又必须要运用问题进行探讨
防卫过当,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指由非罪行为的正当防卫由于明显超过防卫的必要限度而转化为罪的一种形式。防卫过当一般具有如下几种特征:1.刑事的违法性;2.主观过错性;3.损害的扩大性;4.客体的不确定性。 在现代不法理论的框架下,防卫意识仅以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与不法侵害相对抗的事实为必要,因此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不仅包含过失,而且包含故意(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这一观点不仅能与刑法关于防卫过当以发生重大损害结果为要件、防卫过当应当减免刑罚以及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具有同一本质等规定保持协调,而且能够合理地解决假想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问题。
在现代不法理论的框架下,防卫意识仅以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与不法侵害相对抗的事实为必要,因此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不仅包含过失,而且包含故意(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这一观点不仅能与刑法关于防卫过当以发生重大损害结果为要件、防卫过当应当减免刑罚以及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具有同一本质等规定保持协调,而且能够合理地解决假想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问题。 对何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以及“造成了重大损害”的标准与程度的理解
 对何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以及“造成了重大损害”的标准与程度如何,笔者拟作些探讨:第一,从法律规定分析,现行刑法第20条第2款明确载明,“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第二,从侵害的客体上讲,犯罪行为必然是造成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对象造成的危害结果如何,应当是认定犯罪的条件之一。第三,在我国刑法中,除第20条第2款有关防卫过当的
对何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以及“造成了重大损害”的标准与程度如何,笔者拟作些探讨:第一,从法律规定分析,现行刑法第20条第2款明确载明,“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第二,从侵害的客体上讲,犯罪行为必然是造成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对象造成的危害结果如何,应当是认定犯罪的条件之一。第三,在我国刑法中,除第20条第2款有关防卫过当的 缓刑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新罪的不能以累犯论处
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了,在其具备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在一定的考验期间内附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因此,缓刑是有条件的对原判刑罚的不执行。既然缓刑是对原判刑罚的不执行,那就不能把缓刑理解为是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所以,缓刑考验期满不是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对缓刑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新罪的,不能以累犯论处。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和意识形态的日趋多元化形成了累犯制度的客观化渊源
 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和意识形态的日趋多元化,形成了累犯制度的客观化渊源。而探求累犯制度的理论渊源及现实中所产生的累犯问题的相应对策,则是完善刑事立法、实现刑事法治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一、累犯从重处罚的刑事责任根据研究;二、累犯的法域条件研究;三、关于追诉时效完成后能否构成累犯的研究;四、关于单位能否成为累犯的研究。
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和意识形态的日趋多元化,形成了累犯制度的客观化渊源。而探求累犯制度的理论渊源及现实中所产生的累犯问题的相应对策,则是完善刑事立法、实现刑事法治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一、累犯从重处罚的刑事责任根据研究;二、累犯的法域条件研究;三、关于追诉时效完成后能否构成累犯的研究;四、关于单位能否成为累犯的研究。  鉴于普通累犯在司法适用中的概率较高,其制度运作中确有一些应用技术不够精细,有关讨论又能够连带解答特殊累犯和犯罪前科的适用规则,笔者且从刑法第65条规定入手,解读普通累犯(下文简称累犯)的制度要义,并对犯罪前科的认定与适用做简要分析;二、“从重处罚”的内在标准和幅度选择;三、可能判处极刑情形下的累犯情节适用;四、仿效累犯规则运用犯罪前科情节。
鉴于普通累犯在司法适用中的概率较高,其制度运作中确有一些应用技术不够精细,有关讨论又能够连带解答特殊累犯和犯罪前科的适用规则,笔者且从刑法第65条规定入手,解读普通累犯(下文简称累犯)的制度要义,并对犯罪前科的认定与适用做简要分析;二、“从重处罚”的内在标准和幅度选择;三、可能判处极刑情形下的累犯情节适用;四、仿效累犯规则运用犯罪前科情节。  前科株连效应是指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导致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规范性的株连评价,进而导致特定的权利遭到限制、特定的资格遭到剥夺的情况。此种规范性评价立足于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将本应由犯罪人独立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从法律层面上延伸到了犯罪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广泛存在着前科株连制度,不仅对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现实障
前科株连效应是指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导致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规范性的株连评价,进而导致特定的权利遭到限制、特定的资格遭到剥夺的情况。此种规范性评价立足于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将本应由犯罪人独立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从法律层面上延伸到了犯罪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广泛存在着前科株连制度,不仅对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现实障 刑罚理念开始从单纯的报应刑罚观向功利主义刑罚观转变的客观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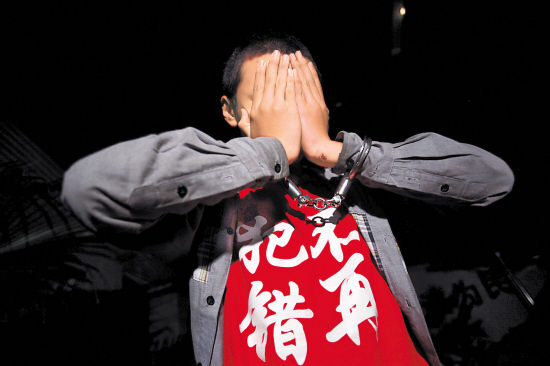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探索和实验,正在成为一种司法改革时尚,基层司法机关的积极实验和探索,为未来体系化的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积累了经验。但是,缺乏理论支撑的制度设计和试行,违背了制度试行的初衷,背离了制度追求的基本目标,有的和前科消灭制度“貌合神离”,有的则完全是“南辕北辙”,甚至是“火上浇油”,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幌子之下,严重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未来体系化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探索和实验,正在成为一种司法改革时尚,基层司法机关的积极实验和探索,为未来体系化的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积累了经验。但是,缺乏理论支撑的制度设计和试行,违背了制度试行的初衷,背离了制度追求的基本目标,有的和前科消灭制度“貌合神离”,有的则完全是“南辕北辙”,甚至是“火上浇油”,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幌子之下,严重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未来体系化 从刑法前科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开始对我国刑法前科制度进行制度性的重构
前科制度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虽然也有其进步意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联系发展的,当我们再衡量一个制度的利弊的时候,最大的可能性是要结合它的时代背景去分析,才会有意义。从以下几点来探讨前科消灭制度:1.前科消灭的主观条件;2.实质条件;3.前科消灭的途径;4、前科消灭的效力。具有前科者再次犯罪所遭受的刑罚打击在刑罚的构成上具有双重的复合性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具有前科者再次犯罪所遭受的刑罚打击,在刑罚的构成存在一定的特点,具体而言,刑罚具有双重的复合性。一、刑罚在量上的复合性;二、刑罚在质上的复合性。前科制度是否与“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再度受罚”的法律格言相冲突
对于“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再度受罚”的法律格言,应当从狭义上加以理解的观点:其一,在某种因素(如行为、结果)已经被评价为一个犯罪的事实根据时,不能再将该因素作为另一个犯罪的事实根据。其二,在某种严重或者恶劣情节已经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予以评价时,不能再将该情节作为从重量刑的标准。其三,在某种严重情节已经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予以评价时,不能再将该情节作为在升格的法定从刑法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对具有前科者再次实施犯罪应当从重处罚应具有哪些理由
从刑法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国外学者认为,对于具有前科者再次实施犯罪应当从重处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1)犯罪人更为重视犯罪价值,则其付出的对等价格相应应当抬高;(2)刑事处罚的耻辱效应可能随着后续处罚而减少;(3)司法错误的可能性减少;(4)刑罚配置更为合理。前科所导致的对后罪从重处罚的根据:立足于社会危害性之上的人身危险性
具有前科而再次犯罪,客观上导致基于前罪犯罪行为之固有社会危害性而评定的刑罚在量上不足以惩罚和预防犯罪,因此有必要在刑罚的量上作适度增加,以使刑罚之痛苦能够抵消犯罪人通过犯罪所获得之乐,从而实现一般预防尤其是实现对于犯罪人的特殊预防,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实现刑罚设置的初衷。 人身危险性因素是前科制度立法设置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何谓所谓人身危险性呢?较为通行的理论认为,人身危险性又被称为“犯罪人的社会危险状态”或者“社会危险性”,指“刑罚法规中规定某行为为应罚行为,即或是无责任能力者阻却刑罚,但对此法有规定刑罚的行为有将反复实施的盖然性,亦构成社会危险性。”它所表明的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
人身危险性因素是前科制度立法设置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何谓所谓人身危险性呢?较为通行的理论认为,人身危险性又被称为“犯罪人的社会危险状态”或者“社会危险性”,指“刑罚法规中规定某行为为应罚行为,即或是无责任能力者阻却刑罚,但对此法有规定刑罚的行为有将反复实施的盖然性,亦构成社会危险性。”它所表明的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 在当前中国报应文化心理现实存在的语境下前科消灭只能是一种趋势
 中国传统的报应刑罚观和预防犯罪刑罚观相互交融,导致重刑主义极大的阻碍了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实现。我们在对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同时,也使我们想到不管给予未成年人如何轻的刑罚,但毕竟未成年人曾经受到过刑罚处罚,在他的人生履历出现过污点,特别是对在校学生,将对他们以后的升学、就业产生影响。于是,我们想在对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同时,能否革除我们标签意识,消灭贴在他们
中国传统的报应刑罚观和预防犯罪刑罚观相互交融,导致重刑主义极大的阻碍了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实现。我们在对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同时,也使我们想到不管给予未成年人如何轻的刑罚,但毕竟未成年人曾经受到过刑罚处罚,在他的人生履历出现过污点,特别是对在校学生,将对他们以后的升学、就业产生影响。于是,我们想在对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同时,能否革除我们标签意识,消灭贴在他们  基于“前科”的禁入并非没有其合理性,一些特殊的职业如教师、律师、军人等,就通常将无违法犯罪“前科”作为行业门槛的必备条件。但我们也看到,这种基于“前科”的禁入在过去明显被扩大化了。在这种困境中,值得关注的是专家与民众之间的尖锐对立。有学者从美国犯罪学上著名的“贴标签理论”出发,认为被贴上“犯罪人”标签的初犯者,由于这种标签(即作为前科的犯罪记录)的存在,将把
基于“前科”的禁入并非没有其合理性,一些特殊的职业如教师、律师、军人等,就通常将无违法犯罪“前科”作为行业门槛的必备条件。但我们也看到,这种基于“前科”的禁入在过去明显被扩大化了。在这种困境中,值得关注的是专家与民众之间的尖锐对立。有学者从美国犯罪学上著名的“贴标签理论”出发,认为被贴上“犯罪人”标签的初犯者,由于这种标签(即作为前科的犯罪记录)的存在,将把